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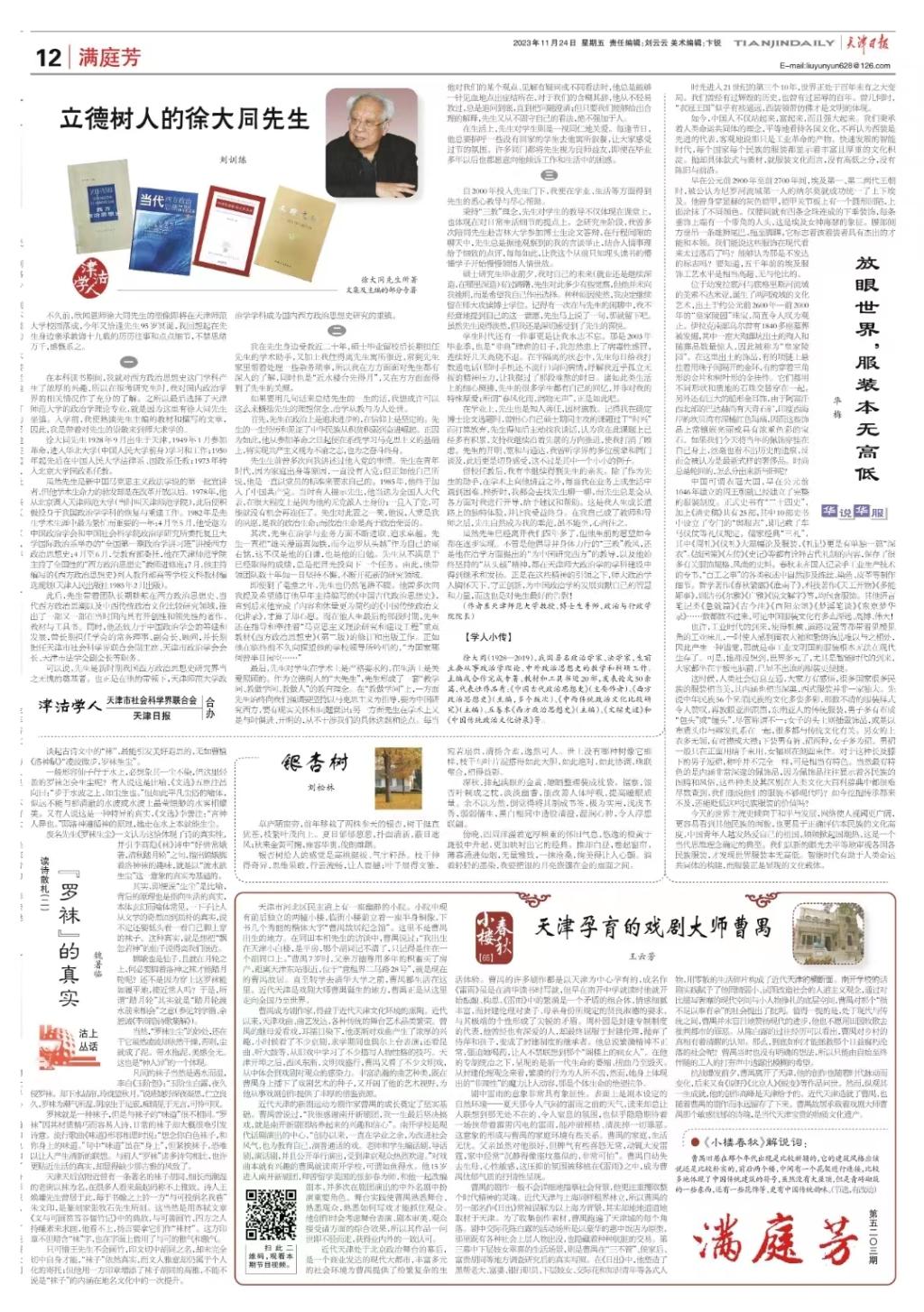
不久前,欣聞恩師徐大同先生的塑像即將在天津師范大學校園落成,今年又恰逢先生95歲冥誕,我回想起在先生身邊親承教誨十九載的歷歷往事和點點細節,不禁思緒萬千,感慨系之。
一
在本科讀書期間,我就對西方政治思想史這門學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在報考研究生時,我對國內政治學界的相關情況作了充分的了解。之所以最后選擇了天津師范大學的政治學理論專業,就是因為這里有徐大同先生坐鎮。入學前,我便熟讀先生主編的教材和撰寫的文章,因此,我是帶著對先生的崇敬來到師大求學的。
徐大同先生1928年9月出生于天津,1949年1月參加革命,進入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和工作;1950年起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國政系任教;1973年轉入北京大學國政系任教。
雖然先生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法學說的第一批宣講者,但他學術生命力的勃發卻是在改革開放以后。1978年,他從北京調入天津師范大學(當時叫天津師范學院),此后便積極投身于我國政治學學科的恢復與重建工作。1982年是先生學術生涯中最為繁忙而重要的一年:4月至5月,他受邀為中國政治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委托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舉辦的“全國第一期政治學講習班”講授西方政治思想史;4月至6月,受教育部委托,他在天津師范學院主持了全國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師進修班;7月,他主持編寫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列入教育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規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
此后,先生帶著團隊長期耕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當代西方政治思潮以及中西傳統政治文化比較研究領域,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在當時國內具有開創性和領先性的著作、教材與工具書。同時,他還致力于中國政治學會的籌建和發展,曾長期擔任學會的常務理事、副會長、顧問,并長期擔任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學會會長、天津市法學會副會長等職務。
可以說,先生是新時期我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界當之無愧的奠基者。也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天津師范大學政治學學科成為國內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鎮。
二
我在先生身邊受教近二十年,碩士畢業留校后長期擔任先生的學術助手,又加上我住得離先生寓所很近,常到先生家里幫著處理一些雜務瑣事,所以我在方方面面對先生都有深入的了解,同時也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又在方方面面得到了先生的關照。
如果要用幾句話來總結先生的一生的話,我想或許可以這么來概括先生的理想信念、治學從教與為人處世。
首先,先生在政治上是追求進步的,在信仰上是堅定的。先生的一生經歷和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到奮進崛起。正因為如此,他從參加革命之日起便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將實現共產主義視為不渝之志,也為之奮斗終身。
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講述過他入黨的事情。先生在青年時代,因為家庭出身等原因,一直沒有入黨;但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一直以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1985年,他終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有人提示先生,他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無黨派人士身份;一旦入了黨,可能就沒有機會再連任了。先生對此置之一笑,他說,入黨是我的夙愿,是我的政治生命;而政治生命是高于政治榮譽的。
其次,先生在治學與業務方面不斷進取、追求卓越。先生一直把“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這不僅是他的自謙,也是他的自勉。先生從不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總是把目光投向下一個任務。由此,他帶領團隊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先生也仍然筆耕不輟。他曾多次向我提及希望修訂他早年主持編寫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直到后來他完成了內容和體量更為簡約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講錄》,才算了卻心愿。而在他人生最后的那段時期,先生還在指導和牽掛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的修訂和出版工作。正如他在臨終前不久向探望他的學校領導所吟唱的,“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閑空……”
最后,先生對學生在學術上是嚴格要求的,在生活上是關愛照顧的。作為立德樹人的“大先生”,先生形成了一套“教學問、教做學問、教做人”的教育理念。在“教做學問”上,一方面先生始終向我們強調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為中國研究西方,要有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先生在學術上又是與時俱進、開明的,從不干涉我們的具體選題和論點。每當他對我們的某個觀點、見解有疑問或不同看法時,他總是能夠一針見血地點出癥結所在,對于我們的含糊其辭,他從不輕易放過,總是追問到底,直到把問題澄清;但只要我們能夠給出合理的解釋,先生又從不固守自己的看法,絕不強加于人。
在生活上,先生對學生則是一視同仁地關愛。每逢節日,他總要招呼一些沒有回家的學生去他寓所敘餐,讓大家感受過節的氛圍。許多同門都將先生視為良師益友,即便在畢業多年以后也都愿意向他傾訴工作和生活中的困惑。
三
自2000年投入先生門下,我便在學業、生活等方面得到先生的悉心教導與盡心幫助。
秉持“三教”理念,先生對學生的教導不僅體現在課堂上,也體現在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提點上。念研究生階段,我曾多次陪同先生赴吉林大學參加博士生論文答辯,在行程間隙的聊天中,先生總是據他觀察到的我的言談舉止,結合人情事理給予細致的點評,每每如此,讓我這個從前只知埋頭讀書的懵懂學子開始慢慢領悟人情世故。
碩士研究生畢業前夕,我對自己的未來(就業還是繼續深造,在哪里深造)有過躊躇,先生對此多少有些覺察,但他并未向我挑明,而是希望我自己作出選擇。種種原因使然,我決定繼續留在師大攻讀博士學位。記得有一次在與先生的閑聊中,我不經意地提到自己的這一意愿,先生馬上說了一句,那就留下吧。雖然先生說得淡然,但我還是深切感受到了先生的喜悅。
學生時代還有一件事更是讓我永志不忘。那是2003年畢業季,也是“非典”肆虐的日子,我忽然患上了病毒性感冒,連續好幾天高燒不退。在半隔離的狀態中,先生每日給我打數通電話(那時手機還不流行)詢問病情,紓解我近乎孤立無援的精神壓力,讓我挺過了那段難熬的時日。諸如此類生活上的細心照拂,先生的很多學生都有自己的回憶,并非對我的特殊厚愛;所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正是如此吧。
在學業上,先生也是知人善任,因材施教。記得我在確定博士論文選題時,曾擔心自己碩士期間主攻的課題過于“時興”而打算放棄,先生得知后主動找我談話,認為我在此課題上已經多有積累,支持我繼續沿著先前的方向推進,使我打消了顧慮。先生的開明、寬和與通達,我曾聽學界的多位前輩和同門談及,此后更是切身感受,這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例子。
留校任教后,我有幸繼續得到先生的親炙。除了作為先生的助手,在學術上向他請益之外,每當我在業務上或生活中遇到困難、挫折時,我都會去找先生聊一聊,而先生總是會從各方面對我進行開導,給予建議和幫助。這是我人生成長道路上的獨特體驗,并讓我受益終身。在我自己成了教師和導師之后,先生自然成為我的垂范,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雖然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四年多了,但他生前的愿望如今都在逐步實現。不管是他倡導并身體力行的“三教”教風,還是他在治學方面提出的“為中國研究西方”的教導,以及他始終堅持的“從頭越”精神,都在天津師大政治學的學科建設中得到繼承和發揚。正是在這些精神的引領之下,師大政治學人胸懷天下、守正創新,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這也是對先生最好的告慰!
(作者:劉訓練,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與行政學院院長)
【學人小傳】
徐大同(1928—2019),我國著名政治學家、法學家,生前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主編或合作完成專著、教材和工具書近20部,發表論文50余篇,代表性作品有:《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主要作者)、《西方政治思想史》(主編,多個版次)、《中西傳統政治文化比較研究》(主編)、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主編)、《文綜史跡》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講錄》等。
來源:天津日報 2023年11月24日 12版